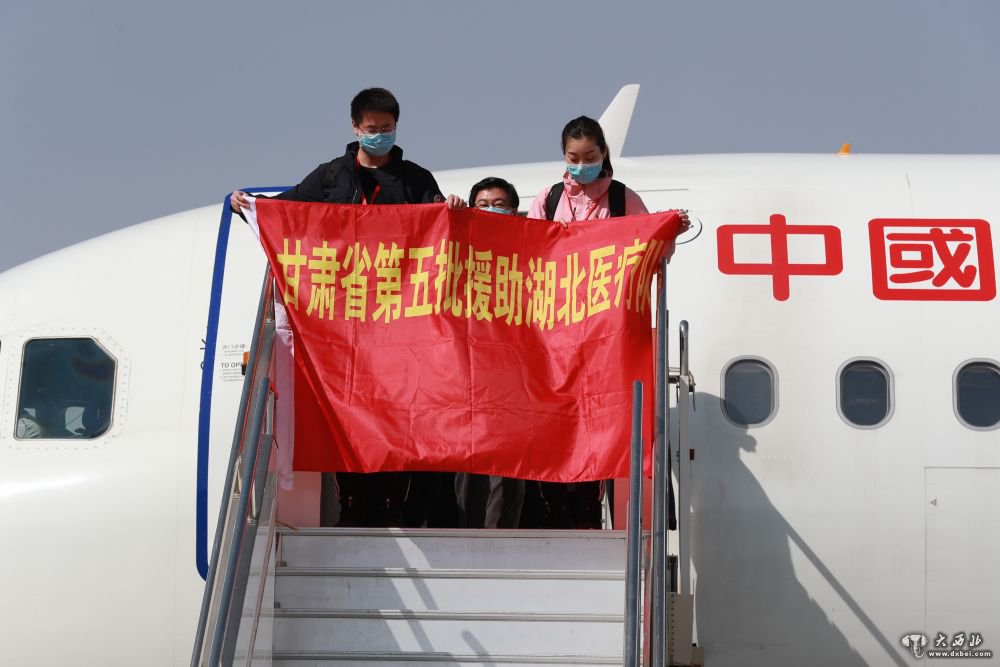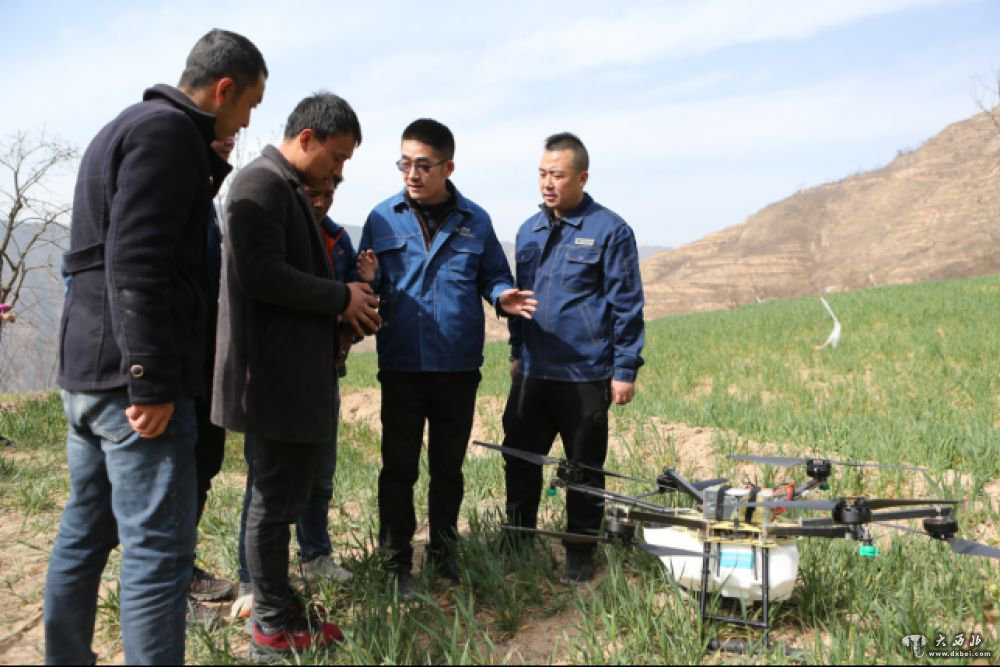我无所谓;反正都是同学。我们大学有七千多个同学。
芝儿与贝贝穿好运动服在接待处等我。
她们长得很好看,你知道,廿岁出头,青春活泼,但是外国女人再美都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,世界小姐也不过如此,高鼻子大眼睛小嘴巴,没有灵魂感,不比中国女子,像孙明媚,简直嘴角都孕带诗意。
她们陪我在校园内跑步。有一条窄窄的跑道的雪被铲清,湿濡濡地,春天相信不会远了。
但是如果没有爱情,春天与冬日有什么分别?
啊我在渡日如年。
我们连跑三个圈子,我觉得兴趣索然。
芝儿撑着腰间:“怎么?阿细,没兴趣?”
“你怎么也知道我叫阿细?”我气问。
贝贝耸耸肩,“每个人都知道。”
芝儿看着我笑,“你是不是在恋爱,阿细?心不在焉的,没想到男孩子也这么痴情。”
“是。”我郁郁不乐,“我所爱的人不爱我。”
芝儿说:“阿细,这是很普通的故事,世上不如意之事常八九。我们喜欢你。”
我埋怨,“你们予我麻烦多多。”
“太不公平,阿细,”贝贝笑,“我们岂不是朋友?”
芝儿喷着白气玩,“我知道珍纳喜欢你,阿细。”
贝贝说:“我也喜欢你,阿细,我不会介意与你约会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不是不感动的。
“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君子。”贝贝笑说。
我说:“君子要回去了。”
贝贝看天空,“天黑得早。”
我把她们送回女生大楼,迎面而来的正是我朝思暮想,梦寝难忘的意中人孙明媚!我又惊又喜,惊的是这次不知道又该如何遭她白眼,喜的是又获得目睹倩影的机会。
明媚手挽着针线篮子,戴一副连指绒线手套。漆黑的眼睛骨溜溜,朝我身上一转,马上避得我远远,往另外一条路上去了。
我眼睁睁地望看伊人远去,跌脚说:“她真当我是大麻疯!”
贝贝说:“阿细,再见。圣诞我们回家,假期后再见。”
“再见。”我说。
芝儿也说:“再见。”
我取过车子,一路驶回宿舍。
因为雪厚路滑,我把车开得很慢,心想:明天要把车子送到车行去,车服上要缚上铁链才行。
咦,那不是孙明媚?为什么一个人踽踽而行?上哪儿去?这么夜了,又冷。
我把车停下来,响号。
她看见车里是我,脸色大变,马上加紧脚步。
我把车窗放下:“明媚,请上车来,我送你一阵。”
她脚步更快。
“明媚。”我一边叫一边把车子加速。
她几乎在奔跑,忽然脚下一滑,摔了一跤。
我一吓,连忙停下车。下车去扶她。
她挣扎看起来,推开我,沉着声音:“不要动!别碰我!”
把我当作什么洪荒猛兽了。
“明媚。”我说:“为什么拒我于千里之外?”
“我不符合你的要求!请你快上车走,”她铁青着脸,“快走,不然我要叫了!”
我既好气又好笑,“你把我当什么?色狠?色魔?好,一不做二不休,你大声喊吧,反正这条路没有人,你叫破了喉咙也没有用!”我马上做一个狞笑,“哼哼哼!”我扑上去。
谁知道她伸手给我两个巴掌,毫不容情。
我气了,一手抓住她的手,“你太不讲理了!我完全是善意,你如果不想与我做朋友可以说个分明──”
她出力把我一推,暗蒙蒙中我脚步一滑,整个人向后倾,是,不错,最不幸的事发生了,我身后是一个大池塘,校园最好的景色,春天有成群鸭子游泳的池塘,此刻结了层薄的冰,我一跌下去,冰“喀嚓”裂开,我听到孙明媚的尖叫,然后是我自己堕水的声音。
我并不害怕。
开头冰水浸过我的身体,我只觉得麻辣辣地,我沉下水,天黑了,我找不到冰破的那个洞,我游上去,用肩膀顶冰,我心中很镇静明白,如果冰厚顶不穿,我就完了。
但幸亏冰很薄,我的头冒出水面。
我叫:“救命!”
路边已经停着一辆警车,四个警员闹哄哄地用手坦探照灯射过来,大声呐喊。
“别怕!”
“支持着!”
“我们马上来,”
但是我一路上撞碎冰块,游到塘边,他们只要把我拉上岸就行了。
我双脚踏到地上,风吹上来,才觉得寒冷,牙齿马上上下双撞。
警察们说:“快!快脱衣裳,脱光!”
我连手指都僵硬了,不能动,浑身痛得针剌般,不禁大喊一声。
他们七手八脚的帮我剥下裤子外套、衬衫毛衣、鞋子袜子,一丝不挂,然后用条大毯子里住我,把我推上警车。
“往哪儿去?”我颤抖着问。
“医院!”他们说:“年轻人,你差点丢了你的命!这么冷的天掉到池塘里,幸亏那个女孩子看见你,又幸亏我们经过,不然,哼哼。”
我说:“谢谢。”
我这时才想起明媚。她现在怎么想?她满意了吧,看我当众脱衣。
到医院当然是例行检查一番,喝了热茶,拿了药。
我没生肺炎。
但重伤风。
卧病达两星期。天天在床上哼哼唧唧。
所有的女郎都来看我,也有些寄卡片与送花来。
我躺在床上度过我的圣诞与新年。
珍纳与莉莉安天天来陪我说话,明媚芳个杳杳。
我非常闷,拼命吃巧克力,体重起码增加十磅。拼命看武侠小说,眼睛都痛了。
我又经常午睡。
睡着以后,不愿醒来,我想我是为想念明媚而病了。
一日下午,我睁开眼睛,闻到一阵香味。
这不是完妹们用的廉价古龙水。
我的心狂跳,连忙转头。
一个女孩子背我站着,在看楼外雪景,乌油油黑发垂在肩上。是孙明媚。
我呆着,听着自己的心跳声。
她缓缓转过头来,看见我已经醒了,吓一跳。
(责任编辑:陈冬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