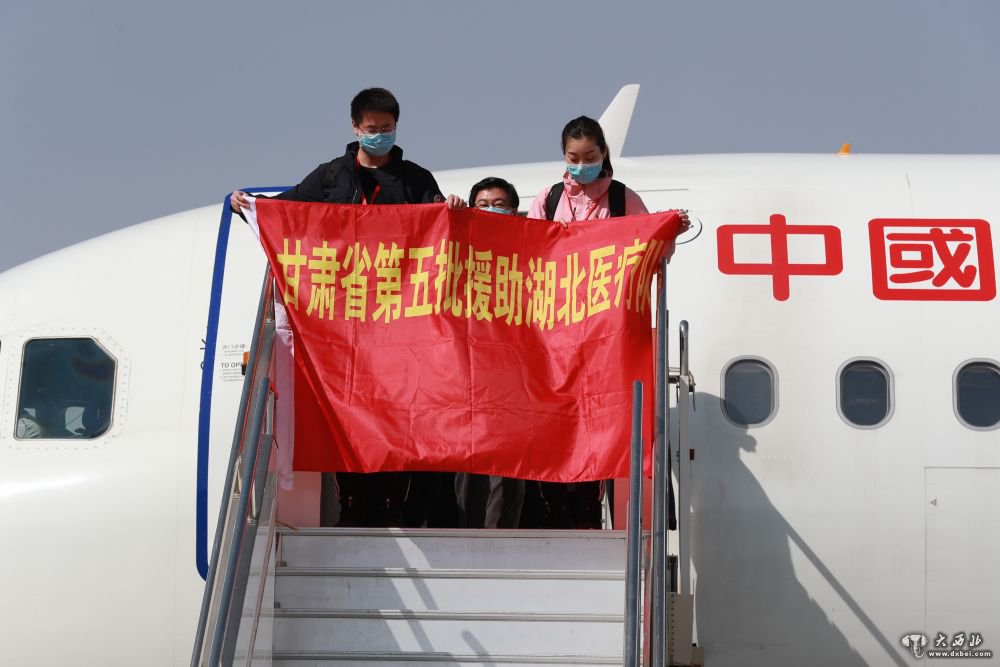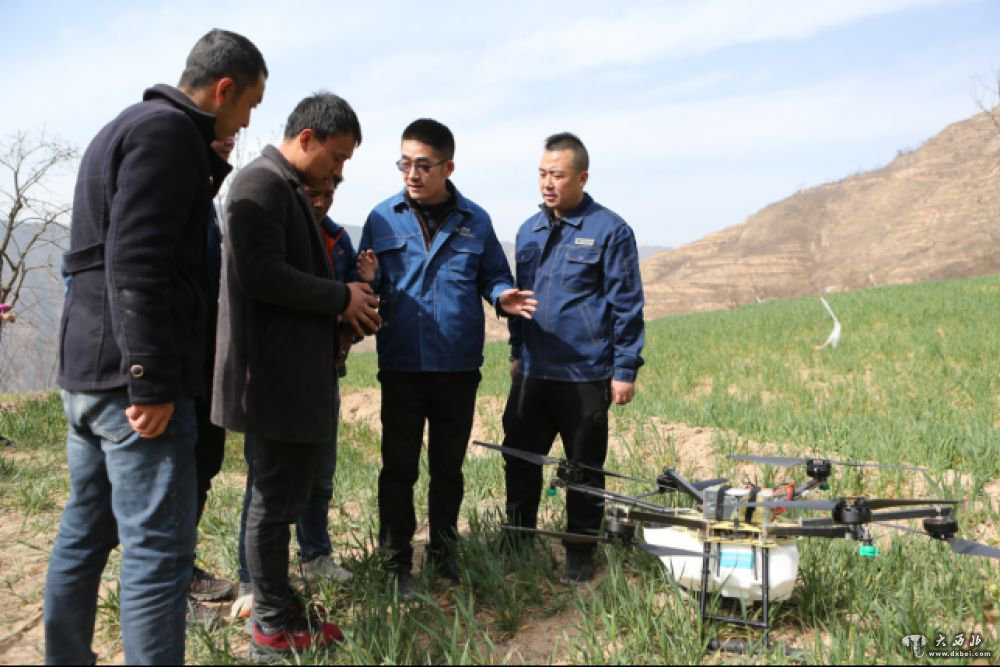这个故事一点都不浪漫。
情节是围绕着老榆树展开的。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棵老榆树来,当年我挥起镰刀,嚓嚓嚓,把榆树外面的糙皮割掉。这当儿旁边有一双好看的眼睛盯着呢,是我表姐白梅,她眼看着我一刀刀将里面金色的嫩肉(嫩树皮)割下来。然后背回家,大铁锅里一炖,味道还行,就是排泄的时候遭罪。
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,1961年的春天。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,那时候全国闹饥荒。不少人便落脚到榆树屯来割榆树皮吃。那棵见证了我和白梅童年时光的老榆树至今仍挺立在砬子河边。
一般我不用老家园子里的厕所,总是寻砬子河南岸深草里,一蹲半天,脸憋通红,不行就站起来,叉腰运一会儿气再蹲下。里面涩糙的榆树皮,赖在肠子上一点点往下挪,存心想把肠子划破似的,好容易露出点头,一呼吸,又他娘的回去了,跟锯似的在那拉我那点嫩肉,都出血了!
撑不住,我没命地喊白梅!我一喊她就来了。其实,她一直躲在旁边替我急呢,害羞,我提出来,性质就不一样了。她用早准备好的两根棍子,分别攥住棍子两头往下拽,我喊疼,她便停下安慰我,声音柔美,内容粗鲁:毛驴,咱不驴!不驴!我小名叫毛驴,这时我没心思斗嘴,早疼得满眼眶泪了。正是春天,又在山野,这份艰苦的工作后,她便鸟一样的飞了去。不一时,飞回来,两手藏身后,猫步来我歪坐的风倒木后,这时,我刚提罢裤子,在那生闷气呢。忽然,她溜到我面前,说:变--大变活人!毛驴变白马!
一时就魔术般的从身后弄出一个花环来,轻柔地扣我头上,蝴蝶就围过来……我嘿嘿地笑了。白马比毛驴受听,另外白马和白梅都姓白啊,我心里受用。我笑,还因为她用手使劲揉我的脸,她的手真细,没臭味,保准是刚在砬子河洗的手,有香味,也兴许是野花的味儿。
我啊啊地喊起来,她也喊。满山谷荡着我们幸福的声音。我一直有个疑问难启齿。后来,借个什么缘头问了,她却不说。我老是猜想她的屁股肯定比脸更白!却遗憾没有机会为她效力。那次,我笑够了歪头叫她:姐?我求她的时候,称呼就变成一个字了。她听我叫姐,立即很警惕的样子,蓝天样的眼睛大了起来,鼻翼也大,扮鬼脸,红嘴唇快速闭合,语调很快:毛驴,想干什么?我想了想,决定迂回一点,说:城里人,不合群!她左手叉腰,右手攥成拳头,忽然弹出食指,点我鼻子上:毛驴!有屁快放!
粗!俗!我又喊了:白梅太粗俗喽!一边站起来朝河那边的砬子上喊着,砬子上就传出了回音:太粗俗喽!我得意极了。但我的问题一直没有答案。有一次,我又想问她,她看见我好奇的架式,竟红脸了,说我姓白嘛!紧跟着话锋一转说:因为我不贪吃!见我不满意样子,她后面的话就难听了:谁像你!馋猪!
我愿意她骂我。妈常说,我上学前那几年,若不是小姐姐管束我,我肯定会把人家的房瓦揭下来。是呵,小姐姐才大我一岁,但懂的事可多呢?我愿意永远和她在一起。
那天下午,我们弄了榆树皮回家,菜刀剁碎,那边一米直径的大铁锅下头灶口,火苗噼啪直响。我坐在厨房的小凳上,双手在膝盖上托着下巴,瞅着榆树皮下到锅里,溅起白亮亮的水花。扭头见白梅自西屋帘里探出头看我,她脸红了一会儿,接着又抿嘴眨眼,嘴唇直扭,我看出来了,八成又是那几个字:毛驴,馋猪。奶奶!白梅骂我!我嚷道。爷、爹娘下地挣工分去了,奶在家做饭,听我喊,奶回头找白梅,白梅早缩回头了。奶便说:俺乍没听见呢?乍就没大没小呢?不叫姐呢?
我撅起嘴,这时,见村干部领进来个生人,跟奶连说带比划,奶的脸色不好看了,他们一起进西屋,不一会儿,就听见白梅哭了。白梅眼睛红红的出屋瞅我半天。我俩都不说话,她跟那俩人走了。我坐在门坎上放声号哭,妈回来劝不停,爹回来后我才不敢哭了。
后来知道,白梅的爸妈都是右派,她妈妈病危,她舅来接她的。当晚我横竖睡不安生。突然觉得枕头边有什么东西硌脖子。凑窗帘那月光下看是榆树皮卷,立马捻亮煤油灯,见是白梅用厨房灶炕的炭画的一幅画:老榆树的树冠挂满云彩,中间是两只蝴蝶,下边是一头张大嘴的驴。
我抱着它睡了,我长大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比这更好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