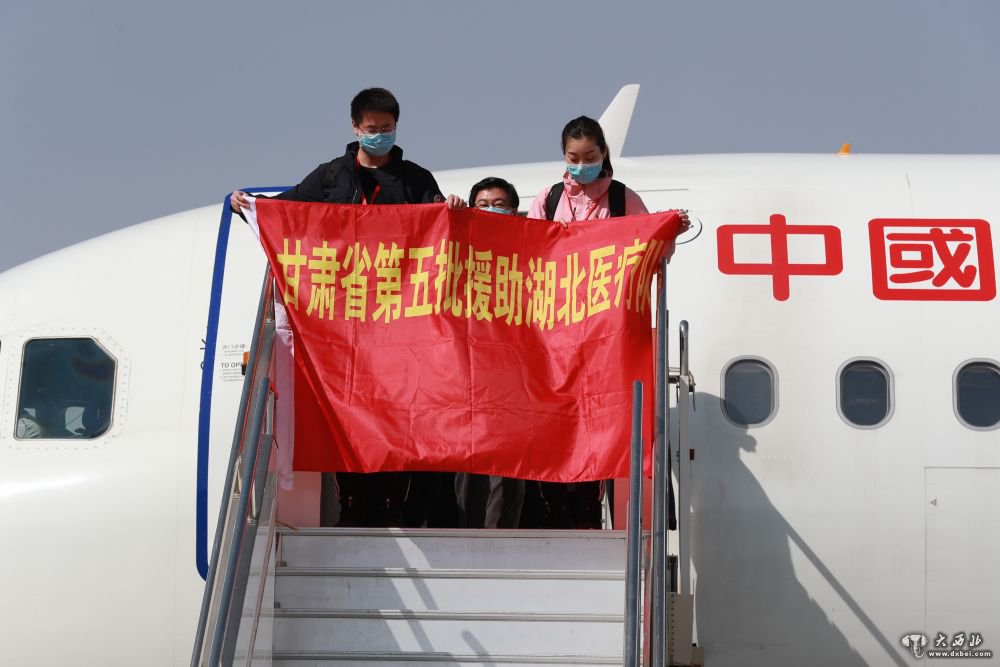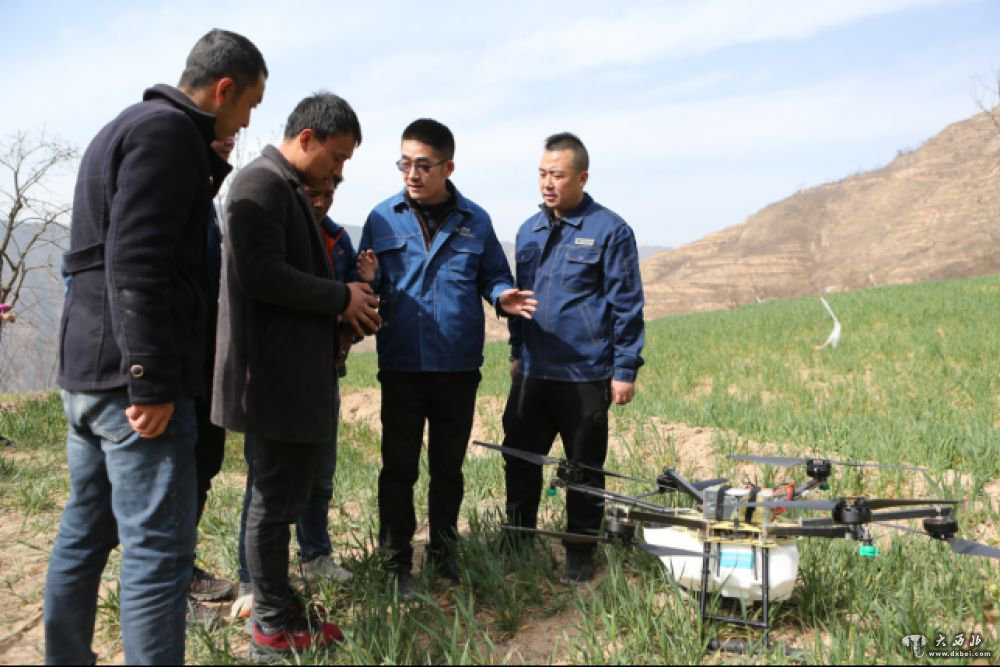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5年去了。在我的岳父刘黔骏忌日那天,我和亲人们又来到他的坟前,向他诉说我们对他的思念。我和他女儿留待最后,边跟他说些悄悄话,边把花朵掰开,撒下点点花瓣;临走,单将一朵玫瑰搭靠在墓碑上。
“爸爸,你是我心中永远盛开的玫瑰!”他女儿说道,眼中隐有泪光。我低声跟了一句:“也是我的。”
不禁回想起我与岳父最初的“神交”.那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春日。据说,他读了我写的一篇万字自述,颇为欣赏,便以他惯常的直率对他女儿讲:“这人很有情义,文笔也不错……还等什么呢?带他到家里来吧,我要见他。”那时,我和他女儿认识还不到一周。
我跟(准)岳父第一次见面交流就感到十分投缘、融洽。看得出来,全然是出于打消我拘谨的用意,他聊起的几乎都是跟我工作、兴趣贴近的话题。后来我的父母来京参加婚礼,他居然当着我的面,对我父母说了一句十分高抬我的话,令我受宠若惊,也非常惭愧。几年过后,有一回我跟他女儿因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执,他不露声色地把我拉到一边,对我说:“深深脾气一上来就这样,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都怪我和她妈妈过去太宠她,把她惯坏了。”
其实我知道,他对自己的女儿有多疼爱。女儿小时候有一次做错了事,怕受责备,就赶紧爬到床上装睡。可他一句话都没说,只是到床边看了看,为她擦去眼泪,留下手帕,然后转身走开,再也不提此事。女儿在他执教的北京五十七中就读那会,有一天上楼时与父亲擦肩而过,随即有位同学对她说:“你爸爸一定很爱你。”她问为什么?同学道:“因为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你。”
岳父嗜烟爱酒,更喜读书、交友,也写得一手好字。他豪爽达观、乐善好施,颇有君子风范。特别是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,他曾不顾自身安危,主动、无私地帮助过许多人,温暖过好些原本孤寂、凄冷的心(不少事情我们都是在他去世之后,从大家的回忆中才有所了解)。尽管他没做过官,没发过财,似乎也没树立过什么宏大的理想、取得过什么骄人的成就,但却赢得了亲友、学生的广泛爱戴。平凡的人生履历丝毫没有削减他在大家心目中人性的光辉。
跟岳父相聚的日子里,最开心的时光是在傍晚,当他招呼我“来两口”的时候。饭桌上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,他常常还会关切地问到我的工作。2005年至2007年我在《科技日报》开设“科学随想”专栏期间,他替我剪下并收存了每一篇文章。有一天,他对我说:“科学上的东西我不大懂,你这篇文章写得好,我看明白了。你应该把这些文章结集成书。”(可我的科学随笔集《星星还是那颗星星》印出来的时候,他已经不在人世了!)2007年春我的科普代表作《幻想--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》出版,岳父翻阅后觉得不错,专门向他原来任教的中学教师做了推荐。2009年初我开始给《北京晚报》五色土副刊写“身边的科学”专栏,时常就文辞问题向他请教,他总是以探讨的口吻跟我说话,让我颇受教益。
岳父亦有愤世嫉俗、脾气急躁的一面。亲友聚会,聊及社会丑恶现象或可气可恼之人,他时常会来几句“国骂”.然而,他又不失理智、冷静与宽厚。他说话、做事总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,也很注意考虑对方的感受。在他去世前两年发生的一件事,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事情的起因已然有些模糊,只记得那天傍晚,岳父专约我到住家对面的饭馆里喝酒,举杯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刚才我不该对你发火,请你原谅。最近我可能是血压有点高,不太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。”
长辈的这个姿态让我深感愧疚,何况还是我有错在先。在他撒手离去几天后,岳母不经意间对我念叨过一句:“你爸特别爱整洁。他可能对你的唯一意见,就是你屋子里书堆得太多、太乱。”可是,岳父生前从未就此当面说过我,我却记着有好几次晚饭后,当我正在厨房里收拾的时候,他特意走过来对我说:“差不多就得了,歇会儿,抽棵烟。”
刚过完70岁生日的岳父毫无征兆地突然离去,对亲友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,同时也给他深爱的外孙尼莫的成长,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巨大缺憾。就在他走的那天下午,3岁的孩子奇怪地望着满屋子面容凝重的大人,却看不到天天相随呵护他的姥爷。有人曾瞧见小家伙在人群中急切地找来找去,又死死揪住一个亲戚的衣角,露出惊恐、忧郁的神色。那一阵他老问:“姥爷哪去了?”我们对他说:“姥爷上天堂去了。”他又问:“姥爷上天堂干吗去了?”我们答:“姥爷上天堂抽烟喝酒去了。”有几次话没说完,眼泪禁不住就流了下来。
岳父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影像,是晚饭时夹菜的场景,尼莫就骑在他脖子上,我给拍的。此前两年,有一天午休时间我回到家里,发现爷俩睡得正酣,尼莫竟然是整个身子趴在他姥爷的胸脯上,我赶忙拿出了相机……
定格了,这些个温馨、难忘的瞬间。此情可待成追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