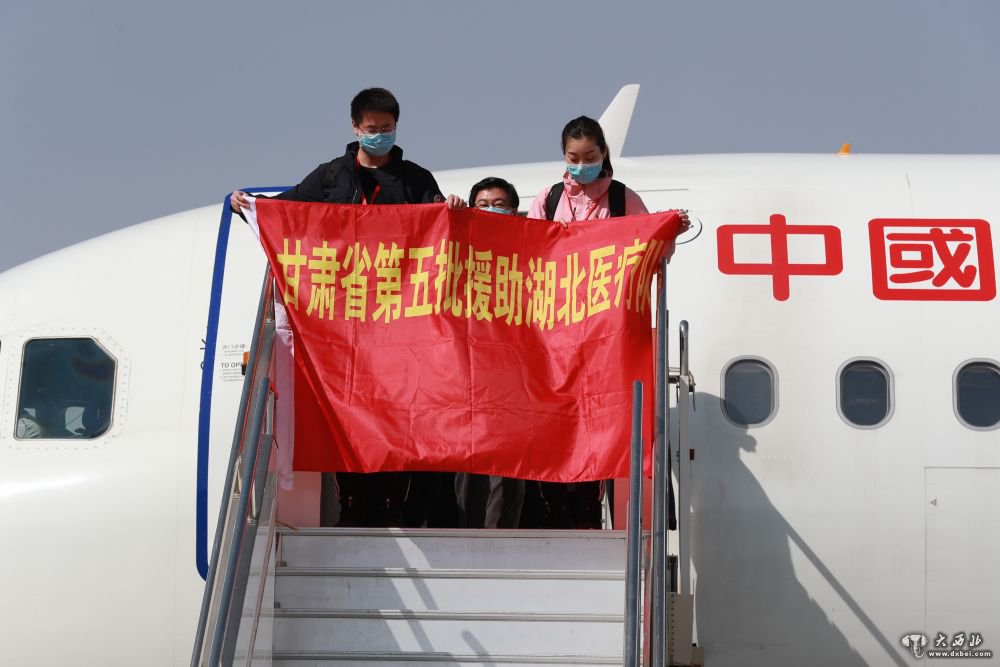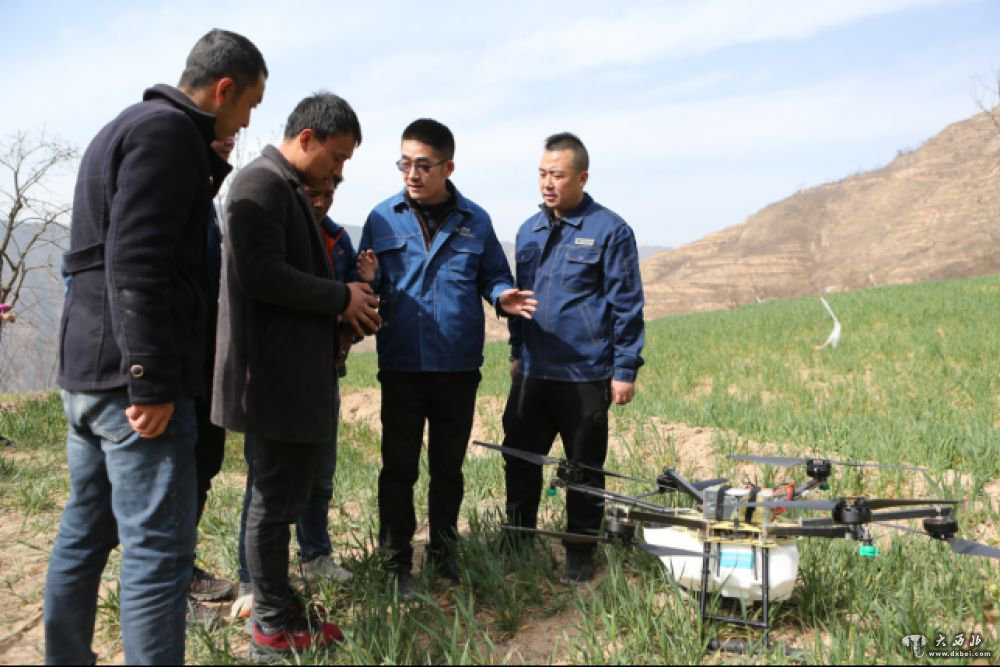我说不出那4个徘徊在三里屯服饰大厦里的清洁工有多穷。她们都三十多岁了,聚在一角商量去吃两碗面条,谁也不敢打头,怕进里面那个装饰着荷花的餐厅。她们每天都拖餐厅门口的地,每天都打扫餐厅旁边的厕所,每天都擦餐厅前面楼梯的把手。要到元旦了,餐厅门口的黑板上写着许多打折的菜名,菜名都很好听。
她们在楼梯的角落里商量了好半天,一个年纪大的才说,怕什么。3个女人跟在她后面,餐厅的服务员吃惊地看着排着队进来的4个蓝衣服。还是那个年纪大的叫了饭。餐厅里灯光很亮,吃饭的顾客不停地看她们,她们就坐在亮处,脸上红红的,高兴地说着话。我隔着玻璃,在心里深深地心疼着她们,脸上却呆呆的,好像我是另外一个人。
我说不出那个扛着铁镐走在建外SOHO的民工身上有多少土。他的眼睫毛都被灰尘压住了,整个人是灰土的颜色*.要过春节了,地铁口附近全是叫卖年货的人,等车的人,挤得走不动。他和他的伙伴们不用挤,人们为他们让开一条路。他们有的人背着一卷绳子,有的人拿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尿素袋子,有的人什么也没有拿,佝偻着腰,裤子抽在半腿,灰土里露出满头扎眼的白头发。
走着走着,扛着铁镐的人在一个卖小猪储蓄罐的地摊前面站下了,他呆看着红底撒着金粉的小猪。卖东西的人说,10块钱,10块钱,我还给你个盒子。队伍里的一个伙伴说,赶紧走,买那个又没用。他说,寄给儿子。看看,他又跟着队伍走了,一步三回头地望着。走到红绿灯那里,他突然又跑回来,什么也没有说,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10块的钞票,把包好的小猪抱在肚子上走了。
我远远地跟着他们,不知道走了多远,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流着眼泪跟在他们后面。北京的冬天风真大,真冷。
我说不出住在北京草场地村的那些出租车司机每天是怎么睡着的。冬天,深夜一点,他们钻进不到一米六的低矮平房里,屋顶上只用砖头压着石棉瓦或者油毡,里面还有孩子的哭声。
我说不出我的父亲的左眼是什么时候看不见的。这个靠种地和卖凉皮供两个孩子上完大学的农民说,街上的瞎老汉不是多得很嘛,去医院有啥好看的,我迟早是要进土的人。
当我在出差的路上,啃着买来的一块馍馍,喝着矿泉水,看到和想起这些不会留下名字的人。我知道,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人,尘土一样地落在我身上,饿了能吃上一碗饭,瞌睡了能有个地方躺下睡觉,能活下去就行了。
我的父亲说,《古兰经》里写,要是福气不在这一辈子,那它一定在下辈子。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放羊,最喜欢听头羊脖子上的铁铃声,只有那丁冬丁冬的声音,让人感到无限的慰藉,也像是给人燃起希望的火花。羊能在厚厚的积雪和彻骨的寒风中行走,给人开辟出可走的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