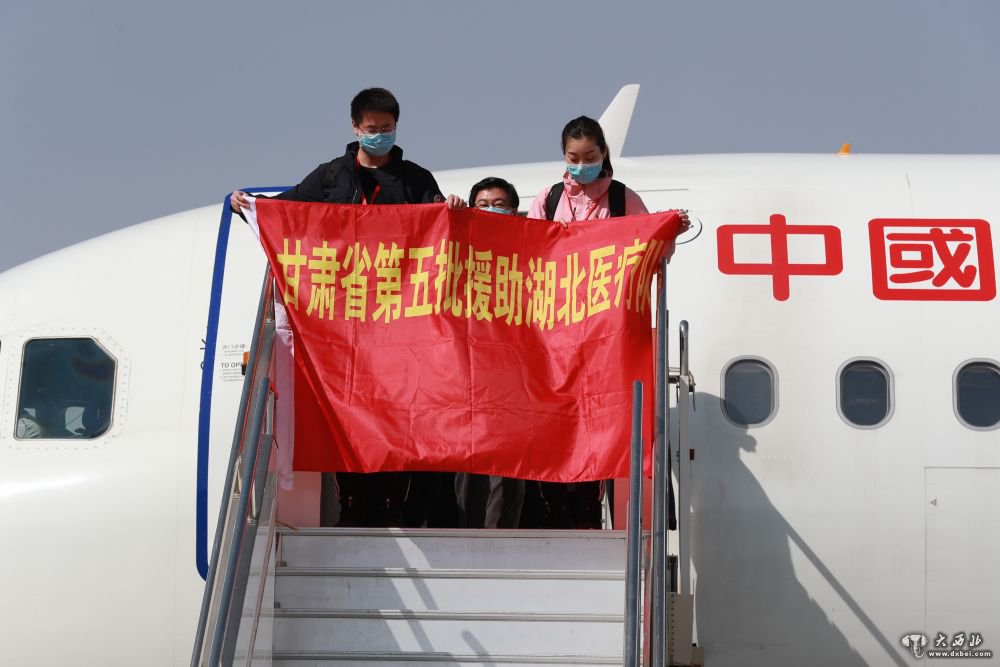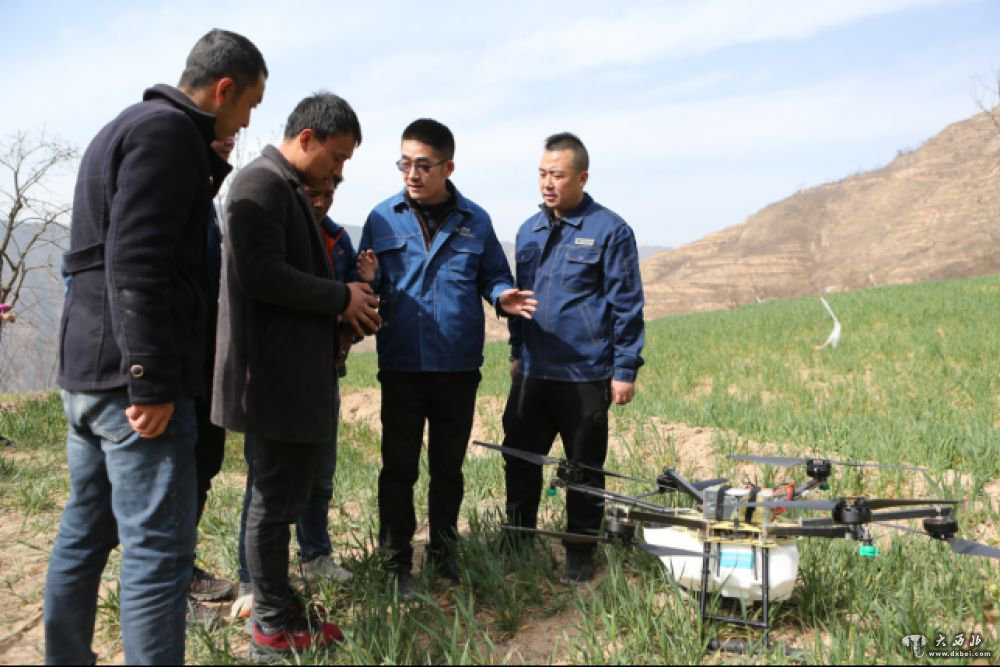我和阿明终于贷款在省城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。父亲在我们领到钥匙的那天,便坐汽车赶过来,说要帮我们装修成最喜欢的样式。
几天后我们去新居,一推门,便看见一个泥瓦匠模样的人,背对着我们,将大桶-乳-胶漆扛进卧室:大概是父亲请来帮忙的农民工吧。待那人将头上裹着的毛巾摘下来。我们才看清,满身尘土漆垢的农民工原来是父亲。
父亲急急地将我们拦住,说:“先等会儿,我拿几张报纸来,要不弄脏你们俩的鞋子。”我和阿明皆红了脸,忙阻止他说:“爸,我们给你帮忙吧。”父亲爽朗地大笑:“你们那手只适合敲电脑,这活,还得我这农民干。”
我不知道,在陌生的城市里,父亲为了买到质量最好又最便宜的油漆和地板材料,是怎样四处奔波。更不知道他在油漆味很浓的新居里,是怎样度过了一整个星期。我只知道,当我们去“验收”的时候,他给了我们最满意的答复。
待将所有家具都运进新居的时候,我们才发现,少了父亲的一张床。父亲却大度地只有一句话:“傻孩子,其实爸一直都愧疚没有钱,帮不上你们,你们肯让我这老头示出点力气,我心里高兴啊。”
就这样,在替我们装修完新居后,父亲一天都没有与我们同住,就匆匆地收拾了他的工具,坐车回乡下老家了。
我打电话给母亲,无意中抱怨卫生间下水道总堵的琐事。3个半小时后,有人摁门铃,门打开,我俩愣住了,是父亲!我吃惊地说:“爸,你怎么来之前也不给我们说一声?”父亲憨厚地笑笑,便换了鞋子直奔卫生间。十几分钟后,父亲忽然在卫生间里大叫 “出来了!”我诧异地走过去,看见父亲正从下水道里拎出一个脏兮兮的塑料瓶子。我这才明白,父亲风尘仆仆地跑来,是为了给我们清理下水道。
我执意要在书房里搭一个临时的床铺,让父亲住一晚。父亲却擦把汗,哼着轻快的小曲,出门回乡下去了。
此后的几年里,只要家里需要,父亲总是以任何维修工都赶不上的速度来到我们身边,帮我们扫除一切生活的障碍。直到有一天,他下肢瘫痪,病倒在床。
我和阿明赶去看他,他朝我们歉疚地笑,说:“丫头,定好了要给你们做一辈子的义务维修工,可现在才几年,就不能动了。”我握着他那双长满老茧、形如枯枝的手,泪流满面:这么多年,父亲无数次来我们小家,竟从来没有在那儿住过一个晚上。
这个世上,再也没有人像我们的父母,肯用全部的爱,一心一意地维修我们的房子。亦没有人如我们这些忙碌的儿女,疏忽到连一张床,都不肯给予生养我们的爹娘。